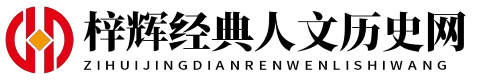(作者:崔永东,华东政法大学司法学院院长)
和谐,是对立事物之间在一定条件下的动态、具体、相对的统一,是不同事物之间的相反相成、互助合作、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关系。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儒家“和为贵”的和谐观最具代表性,但法家也有自己的和谐观,它是用“治”“乱”这样的概念来表述和谐还是不和谐的社会状态的。或者说,儒家、法家都将社会和谐作为自己追求的基本目标,只不过各自为实现该目标所提供的途径和方法有所不同而已。
法家是我国先秦时期最为重视法治的学派,故也主张通过法律途径来实现社会和谐。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商鞅就说:“以刑去刑,国治;以刑致刑,国乱。”所谓以刑去刑,是说通过重刑轻罪,发挥刑罚的威慑力,使人们不敢犯轻罪,更不敢犯重罪,则刑罚可以措置不用。所谓以刑致刑,是说轻罪轻刑,重罪重刑,会使人们不怕犯轻罪,并且会进而刺激人们不怕犯重罪,因此刑罚就会越用越多、越重,这就叫以刑致刑。以刑去刑,会达到“国治”即社会和谐或国家和谐。
商鞅又说:“不刑而民善,刑重也。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而民莫敢为非,是一国皆善也。”不刑而民善,是说不用刑罚而民自觉向善,这是因为刑重的缘故。轻罪重刑,不敢以身试法,因此刑罚即可措置不用。应该说,轻罪重刑是商鞅乃至整个法家学派的一贯主张,甚至可以将此点视为法家的法治战略,只有秉持此种法治战略,才能使民众“莫敢为非”,从而达到“无刑”的目标。站在法家的立场上看,一个“无刑”即不用刑罚和法律的社会当然是一个和谐的社会,而它是靠轻罪重刑的手段达到的。
在先秦时期,儒家主张通过德治的途径来实现社会和谐,而法家反其道而行之,主张通过法治的途径来实现社会和谐。法治的特点是严刑重罚、轻罪重刑。商鞅认为,如果靠道德教化,不但不能实现社会和谐,反而会导致社会混乱。他说:“国用诗、书、礼、乐、孝、弟、善、修者,敌至,必削国;不至,必贫国。不用八者治,敌不敢至。”按照商鞅如此观点,他认为:用道德治国,国家就不能富强,国势也会被削弱,外敌会趁机入侵,导致政权难以巩固,社会难以和谐。这就亮明了法家的立场:儒家的德治不可能导致社会和谐,只有法家的法治才能确保国家的富强、社会的和谐。
正如商鞅另外所言:“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圣人有必信之性,又有使天下不得不信之法。所谓义者,为人臣忠,为人子孝,少长有礼,男女有别;非其义也。饿不苟食,死不苟生。此乃有法之常也。”在商鞅看来,儒家欲通过德治手段实现和谐社会并不可行,但有了法治,那么德治所追求的目标——和谐有序的社会状态自然会实现。这也就是说,法治并不排斥道德因素和道德理想,但要达到理想的道德目标光靠道德教化是不行的,还要靠法治的力量来促成。
那么,实施法治关键靠什么?商鞅的回答是:“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君释法任私必乱。”这就是说,君臣要共同守法、执法,要讲信用,君主还要牢牢掌握实施法治的主导权,绝不能让私心私欲左右法律,否则会导致社会的混乱失和。
商鞅还提出了类似于现代司法平等的理念:“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此处的“壹刑”不但是指统一刑罚的标准,更是指“刑无等级”,即刑罚的适用不会因人的社会地位的高低而有差异。这种在历史上罕见的司法平等理念对促进当时以及以后的社会和谐发挥了重要作用。
商鞅认为,法律是社会和谐的保障,因其具有“定分止争”的功能。“分”类似于今日法律中的“所有权”或“权益”,它由法律加以保障。在商鞅看来,法律确定了名分或权益,就能抑制民众的不当纷争,社会因此稳定和谐。他说:“名分定,则大诈贞信,巨盗愿悫,而各自治也。”法律规定了名分(权益),人们就不会无理争夺,即使是贪婪的盗贼都不会妄取,即使是大骗子也会讲诚信,这就是定分止争的法律所表现出来的威力。
法家的另一代表人物韩非也继承了商鞅的思想衣钵,坚持了法治可致社会和谐的基本理路。他把赏、罚当成法治的两个抓手,认为其顺应了人性,君主善于赏功罚过才能有效推进法治。他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但赏罚必须公正:“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法律是“公义”的体现,旨在维护公共利益,统治者秉公执法才能使民众安定、国家和谐。秉公执法就意味着“信赏必罚”,要求执法者必须律信用,做到赏罚必信。韩非说:“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赏罚必须以法律为依据,依法当赏者必赏,依法当罚者必罚,君主如此做就是积累信用的表现,自然会得到民众的拥护。否则,赏罚不信,则会导致禁令不行、社会失和。韩非法治思想的另一重要特点是强调“明主治吏不治民”,即把治官放在突出位置上,因为官是民的带头人,上梁不正下梁歪,官员依法办事、秉公执法才能使民心安定、社会和谐。
综上所述,先秦时期的法家学派作为我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明确宣扬法治的学派,尽管其“法治”学说与今日的法治理念有很多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也有许多内容与今日的法治理念相通相近。
法家理论的缺陷之一在于其过于夸律的力量,以至于否定道德教化的力量,这以韩非所谓“务德而不务法”最具代表性。尽管法家的法治在整体上并不排斥道德元素,但其天真地认为道德义务完全可以转化为法律义务,因此治国理政只需提倡法治就足够了,不必讲什么道德,虽然和谐社会也是具有一定道德意义的社会(此点与儒家并无根本不同),但那是在厉行法治之后自然出现的情景。这种见识是偏狭的,因为法律与道德毕竟属于不同的领域,法律的“他律”与道德的“自律”毕竟不是一回事,立法也不可能将所有的道德义务都转化为法律义务,这就决定了道德在治国理政中具有法律所不能替代的作用。法家排斥道德教化的作用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实现社会和谐是一个系统工程,单纯依靠法治是难以达到和谐社会的。
法家理论的缺陷之二在于其过于相信轻罪重刑(或谓轻过重罚)的威慑力,以至于丧失了最低限度的人道原则。诚然,轻罪重刑也确实能收一时之效,某些性质恶劣的“轻罪”也理应受到严惩,但长期的、大面积的实行轻罪重罚必然会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弹,进而导致社会的动荡失和。
法家理论的缺陷之三在于其对和谐的理解仅仅限于社会治理的层面,即官民普遍守法而形成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但这种缺乏权利意识的法治并不能促成一种真正优良的、活力旺盛的社会和谐秩序,而更接近于高压下的死水一潭。现代的社会和谐具有更加广泛的含义,它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经济和文化的和谐等等,它是一种动态的、有张力和活力的和谐。
当然,以现代和谐社会建设的视角看,法家理论也有难得的可资借鉴之处:
其一,法家将信用和信用法律提到了治国方略的高度来论证,这对促成和保障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信用要求家与各级干部为政必须讲诚信,在一个单位中,即使最底层的管理人员都必须讲诚信,否则谎话连篇不仅有损单位的形象,而且会恶化单位的氛围与人际环境,使该单位动荡失和。大到一个国家也是如此,除了要求各级领导必须讲诚信外,还要律信用,因为各级领导同时也是手中掌握一定权力者,必须律信用,做到“信赏必罚”,这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
其二,法家提倡整治官员作风。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吏”是当时的底层官员(高层官员称“官”),数量庞大,又与民众有着广泛的接触,其作风如何直接影响到官府在民众中的形象,也直接关系到民众的利益诉求与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法家才将治国的重点和的起点放在“治吏”上。这是有启发意义的。
人学研究网·中华文明栏目编辑:紫天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