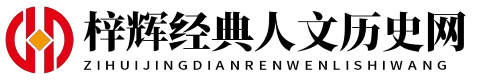(作者:范曾,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研究员、南开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导师)
八大山人之”逃禅“,可说是他在惯看人类不可救药的自私和愚蠢、社会人生的幻化无常以及历史的扑溯迷离之后的最佳选择。他没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和黄道周的血性,起而抗清。八大山人内心的矛盾不会比他们少,人们也决不会景从于他的麾下,替旧王孙去恢复那糜烂透顶的朝廷。他根本不是一个生活的强者。但社稷的沦丧、宗族的溃散,妻儿的死亡,亲朋的凋零,确实他变得异乎寻常的坚毅。天生白恶造就一诗人,同样造就一伟大的、划时代的、万古不朽的画家。
1648年顺治五年当他23岁时剃发为僧,僧名”传綮(qi四声,同‘棨’)“,自号”雪个“。十九岁、二十三岁亡妻丧子。这是他遁入空门的最直接原因。而这些痛苦的化解,则应是他自身修持的胜果,在佛家叫觉悟,在庄子则叫”坐忘“。从混沌的人世得到的一切丧失之后,他来到一个消除烦恼的清凉世界。在这里,莲花次第开放,那是佛国的一片清香。”露冷莲房醉粉红“(杜甫句),在这个世界里,留下一个”冷“字:亦婉如敬安之诗:”心中微有雪,花外欲无春。“这种”‘冷“,是他对社会人生诗性的判断,而不是来自外界的感受;是一种至极的理智与至极的热情彻底融洽之后的”无缘大悲“,而不是世俗炎凉在自身的反映;是辞却懊恼之后的自在,而不是世网羁绊中的我执或法执。
禅一词的解释很多,不太容易从中文找到完整而透彻的对应词。据我的理解,不妨将”禅“译为”慧觉“,亦即智慧的觉醒。
禅,的方法是忘境忘心,内无所欲、外无所求的正审思虑。它需要离开一切言说和实相而证得本心,处处无碍、事事通达,心头永呈一片光明。因此禅是最为圆融而自在的法门。八大山人中年自书”哑“字,本能拒绝对话,是逃禅,也更近禅。
禅宗“不立文字”,因为文字本身是一种言说。离诸言说,“直指人心”,才是禅宗妙谛。所谓:“道个佛字,拖泥带水;道个禅字,满面惭愧。”这与《老子》书的“道可道,非常道”、《庄子》书的老龙吉不言“道”是一个道理。
安察常祖禅师《十玄谈》中说:“莫谓无心便是道,无心犹隔一重关。”表面上在否定“无心是道”,实际是他极而言之,教人们不要一心想着无心:想着无心,便是有心;想着学禅,便是真禅。这是大德高僧解粘去缚、抽钉拔楔(xie一声)的妙悟之言。八大山人之“逃禅”,不是为摆脱世网而逃遁入禅;正相反,是他在解脱我执(烦恼障)、法执(所知障)之后心灵上对禅的逃逸。这种逃逸,便是真正的“无心”。倘若评八大山人画“冷逸”二字的“逸”,用如此解释,则可称与八大山人会意矣。
禅既是自证本心,而本心又是什么?本心之中空无一物。证得那空无一物吗?那是了无尘埃的一片天空,孤明历历的一隅寂照。当此之时,你方做到外息诸缘,内心无喘。达摩谓惠可必须心如墙壁方可入道,意思是那是的心灵,虎豹不能入,水火不能侵,这钢墙铁壁,只有“道”可以进入。八大山人有着这样的追求。他自称“净土人”。八大山人为僧不为僧,他都是禅家。彻底悟禅者,大地皆为,正不必在丛林;钟磐之声,依旧在心头萦绕,也不必在佛堂。
在八大山人那里,佛家和道家的道理,他都渐渐通透,禅家所谓“不修之修”,达到“智与理冥,境与神会,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当一个人能以平常心对待一切色相的时候,那目之所见绝不是奇谲(jue二声)怪诞的所在。唯有这样的人,有可能达到无心无待而与天地精神相往还的境界。禅宗以为,当人处于迷障之时,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当心灵处于历练过程之时,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然则当其顿悟之后,山还是山,水还是水。在八大山人眼中所见,与常人并无区别,那是宇宙的本然存在,那是自然,而禅宗修持的最高境即是自然。
在中国美术史上,的确有真发神经病的,此人便是会稽的徐渭。如果不是袁宏道在石篑的书架上看到徐渭的断阙残稿,恐怕不用到八大出生,徐渭这名字就会湮灭于滚滚红尘。与徐渭相识的梅客生致书袁宏道云:“文长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诗,诗奇于文,文奇于画。”袁宏道则慨叹云:“予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念ji一声)也哉。”大意是徐渭只为人行事,作诗文、写字画,无所不奇,且其奇不可有相类者。“奇”,“偶”之反也,无之不奇即没有相偶也。袁宏道评“文长眼空千古,独树一时。”的确徐渭做到了前无古人,后启来者。殊不知三四十年后八大山人来到人间,正所谓横空出世矣,一洗先贤遗迹,又出生面。八大山人画面物象与徐渭的根本差异是八大山人富哲思、具悲怀,而徐渭则纵豪情、泄愤慨。读八大的画必觉其冷逸而宁静、造型备极生动。艺术的直观性,最是重要,正如诗无达诂,人各有会。我们不赞成论者以白眼鱼鸟即为抗清意识,即为爱国主义。
徐渭之画给人的直感是愤世嫉俗,故看出胸有不平。于是偶有败笔,殊有沉稳之气,这便易流于纵横。而徐渭因才气过人,瑕不掩瑜,终是杰作。八大则能寄宁静于激越,作画之时,心中无挂碍、无渣滓,于是用笔既妍润又峻发,亦若百炼钢成绕指柔,外包光华,内含坚质,线条笔墨无丝毫迫促溷(hun四声,混浊)沦痕迹。《老子》书所谓”善行无辙迹“者,八大有之,徐渭则未得三昧,其间的距离盖不可以道里计矣。徐渭晚岁书画益奇,八大山人晚年书画俞趋宁静;徐渭,书画之侠也,八大山人,书画之圣也。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中国美术史苟无八大山人,绝对也会黯然失色。
我们有必要再进一步探讨八大山人的笔墨。《老子》书有云:”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八大山人似乎永远在做着权衡损益的工作,最后,他是决心永作艺术语言的减法了。唯其如此,语言越简捷而越趋近宇宙本体----道。所以谈八大的笔墨,先谈八大的”无待“。《庄子-外物》有云:"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意之既到,则言亦可忘,这就是中国写意画的本质,而八大山人在这方面臻其峰而造其极。抽象早就是中国写意画家必具的品性,然此抽象断非欧西抽象派画家所指。
艺术当然要描摹自然,其间天才的描摹和笨蠢的描摹,距离正可以光年计。天才的描摹,必投入画家的意志,当画家于天地精神融而为一的时候,那就达到了道家的”撄宁“、”无待“。佛家的”无心“、”放下“的极其幽冥之境,这时画家的意志,就是宇宙的本然。我们有时看八大至极的作品时,心灵的感动是不可言说的,我曾在一篇论八大的文章中写道:”‘无待’,宇宙之大、日月之明、星辰之众,皆顺其自然;天体的运行、万物的繁衍皆随其大化。‘无待’,一切都无所依恃、无所追逐、无所期求。天地的大美,无须言说;四时的代序,毋庸议论;万物生灭,何需置喙(hui四声,借指人的嘴巴)?古来圣贤的本分是认识天地的大美、万物的至理,无为而治,不妄加意志于造化。“我还说过:”八大山人的画,简约至于极致,那是真正的妙悟不在于言,真正的至人无为、大圣不作。八大山人的画渐渐趋近他语言符号的本身,或者换言之,八大山人的画一种符号性的空前伟岸的语言。所谓“士气”的符号,便是简洁清醇、精微广大、高明中庸、扫净一切的繁文缛节、一切的矫揉造作、一切的事功媚俗,那么“士气”的博大、空明、雄浑、典雅便呈现在你的面前。这是八大山人艺术的符号意义,也是中国画的终极追求。“我之所以连篇累牍地转抄自己这段话,只是为了使世人清楚这”符号“二字:”符号“必须是本质的、简捷的、明确的,因为它”本质的“展示着宇宙的奥妙,”简捷的“对宇宙进行描述,”明确的“表达了天地万物冥不可测的本然性质。大朴无华的八大山人的作品,是中国画史上作得最杰出的,也是无以伦比的。八大山人用情至笃,故而能深入其理,至于其性。虽入于”无待“之境而”谁免余情绕“,他总还有对人间的不忍割舍的些许怀恋,这就是他寥寥数笔所倾诉的全部悲悯和恻隐。他虽”无待“矣,然而无奈的八大山人离不开他的生命状态和生活境遇,他毕竟是活生生的人,他需要草堂寤歌、需要三窗北友,晚景有些凄凉,有时甚至饥饿,双手有疾,厨中乏粒。伟大的天才,和伦勃朗一样,他们创造了无限丰厚的,精美的人类精神食粮,但他们却忍受着饥肠的折磨。写至此,不免为先哲一挥悲怆(chuang一声)之泪。
八大山人笔墨的清醇,发源于心灵的”无待“和”放下“,他决不容忍笔墨中剩下的任何污秽。七八十岁时,他早已是人书俱老的通会之龄了。依我之见,三百年之中其可与八大山人联袂者,倪云林绝对是第一的人选。他们的晚年似乎都不再用色,从而为从而为中国至水墨树建极境。”繁采寡情,味之必厌“,此可为千秋为文者戒,亦足为中国水墨画戒。繁采与水墨是有些不共戴天的,失败者包括精于水墨的张大千,也包括步其后尘而钝于水墨的泼彩诸公,更包括咒骂笔墨等于零的中国画坛现代派”先驱“某人。
谈到用笔,我们自会想到”腕力“一词。揆诸两千年的中国画史,腕力能超过八大山人者尚未之见。腕力者,非角士掰腕之力也。长颖兼毫,持于笔尾,悬空挥写,于二维之平面上,以用笔之提压顿挫、轻重虚实,呈万象于三维空间,斯之谓腕力。而其中之杰出者,我们称他为腕力过人。腕力乃丹田之气由臂至腕、由腕至指、由指末神经末梢运转回环、冲波逆折之力。盖艺林之班头,画界之祭尊,往往心灵具不不矜不伐之定力,用笔乃有不思不勉之运转。气者,周流六脉之生命力也,这和肌肉发达与否,毫无关系。不少名家奋斗一生,下笔之际仍有用力猛之病,吴昌硕自不待言,齐白石、潘天寿亦皆难辞。这当然是以八大山人作标准。比较其他人,次数公皆用笔之上选者。尝见八大山人画寻丈条屏荷花,其茎其叶皆中锋自上而下,坚挺婀娜兼之,此画必八大山人悬壁之作,则腕力之神奇,足可为万古之师矣。石涛不能画长线,齐白石一画长线则有枯柯僵丫之感,就线条而言,比八大山人相差一大截。
至于八大山人之构图,断无造险之愿。古往今来,于《老子》书”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老子--第二十八章》)之参透,无过于八大山人者。知此二者,则”黄金分割“、”三角形“、”不齐之齐“、”齐之不齐“种种高论均可避舍;而量以尺寸、左右比划,然后下笔,皆愚人自缚,绝非构图要义。”位置“当然重要,而”经营“,至少不是八大山人所愿为者。”知其白,守其黑“指知阳而守阴,知刚而守柔,一切处于畜势待发之状态。而此种状态则为八大山人感悟所致,不用刻意为之。八大山人于构图称大作手,无处而不可,无处而不适,如流泉之注地,轻云之出岫,如烟生霞飞,雪飘霰(xian四声)落,了无定则。最迷人处正八大画面之空白。一条小鱼、一只雏鸡、一块石头,背后是几十倍大的空白,事物宛在浑然天地、寥廓宇宙之中。八大笔墨之精良,形态之妙造,有不可言说之美质在。蜷曲的动态,预示着高翔;美妙的笔墨,纯发乎心灵。八大山人把“白”作为“黑”的依存、作为“黑”的相生发的必要条件,八大山人岂止在以“黑”造象,更以“白”造境;而八大山人所造之境往往能将我们引向那众妙之门,心灵于无何有之乡作逍遥游。
人学研究网·中华文明栏责编:紫天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