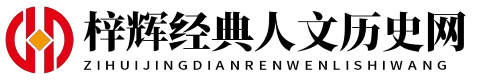(作者:王立新,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作为明末清初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王船山以一介书生,发震古烁今之论,砥砺三百余年之士人精神。章太炎称道:“当清之季,卓然能兴起顽懦,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家而已。”这个倔强孤愤的读书人,一生究竟遭遇过怎样的坎坷?他的生命,对当代知识分子熔铸独立人格、探索价值真理究竟有何启示?经王立新教授授权,凤凰国学特摘录其著作《从胡文定到王船山——理学在湖南地区的奠立与发展》中的章节《船山生平述要》刊载如下,以飨读者。
船山先生(1619——1692)姓王氏,名夫之,字而农,号姜斋,中年时曾自称“一瓠道人”,更名壶,晚岁仍用旧名,因所居在“湘西蒸左之石船山,故有是称。
王氏系出太原,本居扬州高邮,至船山七世祖始居衡阳,遂为衡阳人。船山父名王朝聘,字修侯,因系心朱子之学,而以武夷山为朱子“会心之地”,遂自号“武夷先生”。万历四十七年三月,明兵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辽东经略持尚方剑杨镐兵败萨尔浒,损兵近五万,亡失马驼、器甲无数。后金主努尔哈赤遂乘胜攻克开原、铁岭等,灭叶赫,至此,海西女真扈伦四部俱亡于努尔哈赤。是岁九月初一日子时而船山先生生。
船山四岁,入家塾,从长兄石崖先生介之读书。明辽阳、沈阳尽陷于后金,明既以熊廷弼经略辽东,而天启皇帝信重阉宦魏忠贤,妄杀无辜善士。船山七岁,魏忠贤兴大狱,使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等死于非命,又将星等削籍除外,毁邹元标、孙慎行等讲学之首善书院,榜东林党人姓名顾宪成、李三才、星、高攀龙、魏大中、荐、孙丕扬、邹元标等姓名,以示天下。船山八岁,魏忠贤续兴大狱,使邹起元、周顺昌、高攀龙、缪昌祺、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或投水或死于狱中,并冤杀熊廷弼。是岁,后金努尔哈赤死,第九子皇太极登位称汗。船山八岁,熹宗死,思宗朱由检即位,改明年为崇祯。思宗思振天下之衰,而清除阉宦,魏忠贤畏惧自缢死于凤阳。崇祯元年(1628),以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陕西农民大规模开始,数岁间天下尽“贼”:左挂子、高闯王、大梁王、神一元、神一魁、满天星、金翅鹏、不粘泥、点灯子、双翅虎、紫金龙、紫金梁、闯塌天、小曹操、革里眼、左金王、射塌天、混世王、改世王、过天星、滚地龙、老回回等名目繁多,不胜枚举,加以李自成、张献忠等,同时又有山东游击孔有德等叛乱,而朝廷之内,则既腐于熹宗与魏忠贤,外则后金之逼日甚,明廷实已癌症晚期。
崇祯五年,船山十四岁,入衡州州学。船山先生“颖悟过人,读书十行俱下,一字不遗。”
崇祯十四年,张献忠破襄阳杀明襄王、李自成破洛阳,杀明洛阳王,又破南阳,杀南阳王。清兵攻明锦州,洪承畴以马步军十三万增援锦州,皇太极亦亲往援锦州,明、清两军大战于松山,洪承畴被皇太极围于松山。而荷兰人则于是岁抢占中国。
崇祯十五年二月,李自成破襄城,并于次年于襄阳建立政权,以“奉天倡义大元帅”号召天下。而洪承畴既降于清,祖大寿亦于三月以锦州降清。清兵休整之后,分道入塞。张献忠攻陷武昌。
是岁,船山与兄石崖先生同登乡榜,冬,船山往武昌参加会试,行至南昌,道阻而还衡阳。
崇祯十六年五月,张献忠攻陷蕲州、黄州、汉阳、武昌等,尽杀所至明宗室,号“大西王”,因畏惧李自成之逼,遂放弃湖北转向湖南,八月破岳州、长沙、衡阳等,九月又破宝庆(今邵阳)、永州,十月破常德,旋入江西破建昌、抚州等,后转道进四川。而李自成则于同年九月与明军主力于豫西襄城决战,明军从此丧尽围剿农民军之力。
张献忠攻陷湖南衡州时,试图收拢士大夫之心,以为己用,王朝聘落入张献忠之手,船山“自刺身作重创,敷以毒药,舁至贼所。贼不能屈,得脱于难。”
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三月,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煤山,明亡。明守关将领吴三桂初降李自成而复叛,李自成亲统兵夺关,吴三桂暗引多尔衮,剔发称臣,多尔衮率十五万大军突至山海关,李自成兵败,于四月二十六日撤回北京,二十九日于武英殿称帝,三十日下令焚毁紫禁城宫殿和各门城楼,率军撤离北京。五月二日,清兵入北京,四日,清命官民等为明崇祯帝服丧,后为造思陵。
以李自成与多尔衮对明之不同做法,已见李自成绝无久据江山之理。以胸怀而论,则既胜而不能待败者以礼,而惟以破坏抢掠之能事,此流寇习性。以策略论之,则只知摧枯拉朽,而不知借枯朽以摧拉。李自成本先行一步得北京,清兵盖深悔迟缓,而李自成既不能且无决心保北京,又不能联合张献忠使共襄大事,旋即焚烧、逃离,客观上等于助清以夺明江山,同时又为丛驱雀,故多尔衮入北京,明遗文武官员俱出城五里外跪迎。尽管无耻,实亦无奈。以张献忠论,则既畏惧李自成,且入四川,试图以四川为根据而与各有天下一部份,则其割据之心,始终未尝稍待。使其得手,其狼藉未必在李自成下。
船山闻崇祯自缢,数日不食,作《悲愤诗》一百韵。
五月十五日,明福王即位南京,改明年为弘光元年。令东阁大学士史可法督师扬州。十月清福临于北京即皇帝位,以顺治为纪年。南明内讧激烈,清军乘势破扬州、入南京、取无锡、下苏州,弘光闹剧结束。十一月,黄道周、郑芝龙等扶明唐王监国福州,二十七日称帝,以隆武为年号,唐王赐郑芝龙子郑森姓朱,名成功。同时又有张煌言、钱肃乐等拥立明鲁王监国于绍兴,两王各拥重兵,又各自专主一方,互不相让,几成水火之势。
张献忠则在清福临即位之次月,攻占成都,建政大西,称帝设官,也算圆了皇帝梦。而李自成则携重兵一路狂逃入于陕西,试图走从前道路,忽出忽没,东西跳梁,避强攻弱的游击式生活。被清兵大败以后,焚烧陕西宫殿逃入湖北,于顺治二年五月初四日,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被地方土豪所杀。结束了自己以劫掠、烧杀为主要内容的一生。其余部分而为二,一以郝摇旗为首,暂投明督师何腾蛟于湖南;另一部由李自成侄李锦(亦名李过)率领,投明巡抚堵胤锡,欲效力而抗清。张献忠则拒绝清人之招。清兵为反抗则有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之实。
是岁,理学家刘宗周绝粒断饮以殉明。
顺治三年十月,张献忠于七月撤出成都再入陕西,与李自成想法一样,试图以出没无常、反复无定的方式以图久存,十一月二十四日为清兵击杀于西充凤凰山。余众由其四个“义子”孙可望、刘文秀、李定国、艾能奇分别统领,继续与清兵周旋,苟延残喘以行割据之实,后投南明永历帝。
清兵于八月俘获隆武,押至福州而自死。十月十四日,明桂王在明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等拥立下监国于广东肇庆,并于十一月十八日称帝,号永历。而原明鲁王弟则在苏观生等拥立下,已于此前十三日称帝于广州,建元绍武。广州攻肇庆,自相以快己意。二十一日,清兵破广州,绍武与苏观生皆死,永历逃奔梧州。
十二月,降清将领郑芝龙子郑森,即郑成功,既受姓名之赐而感恩,起兵抗清。
船山自甲申之后,曾走湘阴等地,与南明永历朝联系,有图复明之举。顺治四年冬,王朝聘卒。顺治七年,船山投南明永历朝于广西梧州,充行人司行人。
其间左良玉部将金声桓、高杰部将李成栋既已降清而复叛,与南明永历帝联合,抵御清兵。李自成侄李锦病死,余众由其义子李来亨统领。
顺治七年十一月,清定南王孔有德破南明桂林,南明宰相瞿式耜被杀,永历帝走南宁。清兵破舟山,明鲁王走厦门依郑成功。
顺治十六年,清平西王吴三桂攻破成都,李定国护永历帝入缅甸。顺治十八年(1661)十二月,吴三桂获永历帝,并于次年四月杀之于昆明,郑成功收复。康熙元年(1662)六月,南明将领李定国,闻永历帝被杀,悲愤而死。李定国盖为李、张两支农民军中真正有忠义心之人,其行与死尚为有益,余则几不能论。康熙二年时,李自成部下刘体纯、郝摇旗等仍在夔东一带抗清,至十二月而皆败死,李来亨则于次年八月战死。有以刘体纯、郝摇旗等为不屈死之说,实则此辈原本不知不屈为何物,至此当或降或散以保命,虽不足论,亦不足责。而依然如故,实已成扰乱国家秩序,徒使从者无益送命,且又祸及生民,授满清以杀人口实而已。
窃谓南宋之亡与明亡不同,宋行仁政于民,而知识分子颇受看待,崇尚孔孟以承继传统,维护汉民族文化之尊严,此其义之正也。其亡则外强所致,非由内自溃也。明则不同,明皇既视知识分子如草芥,而万历、魏忠贤等害贤无度,天下精英死于非命者不计其数,如此残酷,宋人所不敢想。明于此前既信阉宦刘瑾等,残杀忠良自已不必多论。仅此者,则其不能代表中国文化之正已然明昭,不必分说而有识者自能知。明政之暴,导致士人心伤气沮,教化不行,加以横暴征敛,遂使农民遍于天下。此其罪不容赦,更何正统之自认?崇祯虽有振兴之意,然其习祖宗以来多疑忌、少恻隐之恶习,且事已然无可为矣,以身殉社稷,不过对血统之来,作一交待而已。孔子之嗣在濂、洛、关、闽,不是衍圣公。彼崇祯者,朱元璋之血胤而已,断然不可成为中国文化之象征,亦无以真正代表中华民族,最多只是汉族人所建立的一个非法政权的执政者而已。
至明亡而后,则宗室纷纷在各路官员拥立下称帝,又互相厮杀,以使清兵得隙而各个诛除,徒遗天下后世笑耳。至如李自成、张献忠辈,皆剽掠、骚扰成性,而究其所欲,则皆烧杀以外,不知尚有何事可作。其无知、无识,而既不堪命,侥幸一逞而已。败亡则焚烧,不知其所烧者既为祖先遗产,又不知既烧之后,清人还可复建,复建则愈伤民力、国家财力,只不过快私愤、呈残暴而已。彼等唯思自存,而心中无片时少刻存装天下生民与历史文化,所谓“均田免粮”,掩人耳目以哄骗参军而已。其徒众后竟又与南明联合,以“抗清为名”以图久存者有之,其尤者如孙可望,尚有欺永历以自称帝之心,真无知、无耻之极矣!惟李定国例外,余则既不知义,何以“义军”称之?
对比而言,文天祥之死,为以身殉道,得其所矣。刘宗周则守一身之节,除此之外,其死别无意义。蕺山黄梨洲通达此理,故其存生以究古今帝王之害,昭示天下后人,使知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
船山先生于中年以前,盖因之痛,思有以作为,遂入南明任职,且尝有暗图恢复之想法与行动。至中年以后,船山痛定思之,则有“天下非一姓之私”,而亦非一姓所能私之突破,遂使思想大进,总归传统,以道殉身,遽至高山仰止之境,遂不再以恢复明朝为职志。
康熙十年,方以智(1611——1671)卒。方以智是安徽桐城人,与船山有交,尝私下联系船山,欲为复明之计,船山知不可为,暗示以人各有志。方以智因曾与西方传教士有较广泛接触,故其近代自然科学知识较丰富,盖对船山于此方面有所影响。
康熙十二年十一月,吴三桂举兵叛乱,不久,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加入。三藩之乱既起,江南又无宁日可度。一时间湖南沅州、常德、澧州、长沙皆为吴三桂所据,不久又攻陷岳阳。湖南震动,而船山先生出避于外。船山先生此间往复于湘乡、长沙、衡阳等地,以躲避吴逆,而人有疑其暗自联系友朋欲举事乘机复明者。康熙十七年三月,吴三桂僭号于衡州,其党有知船山名者,嘱船山为作《劝进表》,船山拒绝之。八月,吴三桂死,罪大恶极之一生结束,清圣祖玄烨八岁继位,是即康熙。16岁开始亲政,亲政之次年,以计擒权臣鳌拜。以古今少见之神武,乘吴逆之卒,大起诸路兵,迅速灭其残党,于二十年底平定三藩之乱,并于二十二年七月,使郑成功孙郑克塽纳表请降,八月,收复。这一年,是公元1683年,船山先生六十五岁。
此后数年,船山先生略得安宁。康熙二十八年,康熙帝于已数败俄贼之基础上,与之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正国界以格尔必齐河以南,包括外兴安岭以东至于海。是岁,船山先生七十一。康熙三十年,清衡阳郡守以官方身份送帛、米与船山,船山辞其帛而受其米,次年正月初二日,船山先生卒于家。
船山一生,身遭国变,虽欲有为而无以振之。痛甲申而仕永历,恶张李而厌吴逆,躲兵避难,藏身衡岳,栖身傜洞。其时则阴霾蔽天、干戈遍地,血腥扑鼻,撕杀振耳,追捕搜求,随时可至,东躲,居无定所,身世遭逢,于此极矣。
然若仅此身艰,尚不足称。遭逢乱世而避兵乱者,古今并不缺乏此种遭遇。而船山独以此称者,盖其心之苦也。船山原本也是常人,少年时代尽管颖悟超群,究其心志,不过读书明理,科举入仕而已。遭逢明社之难,始激发出民族主义,遂至奔走呼号,欲以此身为拯救之资,不谐,则退而研习,乃知天下皆器,而器者,所以载道者也。返身归于传统,遂从以身殉道之自冀,改易途辙而勇担以道殉身之大任。
余尝谓“文天祥不死当指,王船山轻死有罪。”盖天祥为赵宋宰相,宋则崇道重儒,体恤天下,敬待士夫,既得义之正,则天祥死之,为大宋有道,为道舍身。船山返归传统既久,则已然化于其中,成为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而尤其是儒家人文精神的现实化身。如此,则其果若轻死,视斯文之坠堕若不相干,则罪莫大焉!天下既已无道,则其所为,故当为道存身,而不得以身殉无道。
船山“以不能言之心,行乎不相涉之世”,担此礼乐复兴之任,以身从之孤苦为励心之资,自述自话,自生自世,时人虽有相识,而无有能知其心者。其以孤独寂寞为生存之需,古今中外,绝无仅有而已。
船山既亲历甲申,目睹后来明室遗臣、亲王等之卑劣行径,乃知彼等心中原无天下与苍生,惟有一身荣宠、一姓得失而已。船山又由此溯及前明各代,乃深认历朝统治者不过为一姓利益争夺篡杀而已,其结果不过使生民遭涂炭,圣学隐晦而不明,大道黯然而难彰。于是,乃知天下非一姓之天下,而天下人之天下也,天下人者,非帝王之使奴、王侯之牺牲,匪盗之祭享,而圣贤之血嗣,上天之子民也。
船山既生为明民,则无以与清同其流,故当其壮岁之时,尝“抱刘越石之孤忠”,奋身以求恢复,当其不可之时,又拒不剔发,晴日撑伞,行以木屐,有所谓“头不顶清朝天,足不履清朝地”之说法。然船山既知华夏之真在于文化,又见康熙神武冠古今,且卫疆守土,除三藩、收、平定葛尔丹叛乱,驱逐俄罗斯贼寇之侵扰,遂于晚年有受清朝赠米之实。此则表明船山已食周粟,故其子敔可为清朝贡生,且尝入幕提督府。盖船山晚岁已有以文化而不单纯以血统论种族之意。此盖“希张横渠之正学”之后,渐有深体而转变。尽管这种转变较难为世俗所理解,但船山既甘以孤独为生,世俗之论自不在其所虑之中。
船山自题观生居之壁云:“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船山将自己活埋于中国传统之中,因有船山之活埋,而中国传统又发新枝,活力重新得以更加充分之展现。船山七十岁时,画家刘思肯为作小像,船山自题《鹧鸪天》一首:
把镜相看认不来,问人云此是姜斋。
龟于朽后随人卜,梦未圆时莫浪猜。
谁笔仗,此形骸,闲愁输汝两眉开。
铅华未落君还在,我自从天乞活埋。
船山舍命投身中国文化,因得中国文化命脉之传,中国文化亦因此而慧命得续。船山在不可想象之艰境中,握天枢,争剥复,用中国传统的力量,“创造了一个生命的奇迹。” 同时又以自己的生命,创造了中国文化的一个奇迹。此则客观言之。
若以船山心态而论,则其自谓噩梦一生,生于噩梦之中,遭逢噩梦般之巨变,以噩梦般的心情食息人世之间,仰观俯察,所见、所闻、所遭遇者,尽皆噩梦般事、噩梦般人。为政者和欲为政者,皆为利欲而互相攻伐,致使山河破碎、生灵涂炭而不恤。当时所谓士人者,或首鼠两端以为一身之谋,或结党营私以图一心之快;更有甚者不以羞耻为耻,落胆丧气,纳款腥膻,奴事叛逆,伦常殒堕而不救,斯文扫地而不挽。人世之污弊,未有至于此极者也。
船山以清醒之明,行走噩梦世间,心灵之苦,无有可以纾解之途。既而全身心投诸学术,则其学既精考据而不流于章句、训诂之烦琐,又邃于思而不僭以一己之私意。船山“忿士大夫违道趋利,祖袭申商余绪,以破坏国家之元气,故其言奋发蹈厉,如惊雷之破蜇而出,听者莫不悚然动容。”
然船山非故为高论者,王闿运说:“王夫之论史,似甚可厌,不知近人何以赏之?” 如此说法,实应船山湘人无党之论。然湘人之无党,多非出于公心,乃往往出于“意气之偏愎” ,其相互不服,以争高下而互相诋毁者甚为普遍。此种情况,郭嵩焘既曾因乡人不助其积极为船山请从祀孔庙并于长沙妙高峰建祠堂,而慨叹乡党之不重乡贤,对湖南大失所望,从而不再抱有信心。“吾以山长创建船山先生祠,一二无识之议论屈挠之有余。楚人好议论,而学识猥陋大率如此,可笑、可叹。”
嵩焘与湘绮不同,其于船山史论,则谓“若东阳葛氏《涉史随笔》、崇安胡氏《读史管见》,或因古人之事,传以己意,或逞一己之辨,求胜前人,是非褒贬,多失其平。自明以来,论说益繁,大率不外此二者。独船山氏《通鉴论》、《宋论》,通古今之变,尽事理之宜,其论事与人,务穷析其精微,而其言不过乎则。嵩焘尝欲综论元、明,以附船山之后,而未敢遽也。” 郭嵩焘奏请船山从祀孔庙,恐自己立论不足取信,希望湖南省为出面上书一助,致信巡抚等,而“省城诸公凡三十余人,无一回信者。”嵩焘由此深憾乡党之不重乡先贤,“其待二百年前乡先达、理学名儒如此,于并世之人何有哉?” 湘人如何评价船山本属另外一事,因为船山之意义,绝非湖湘一隅所可局限。
船山自知已得中国文化命脉真传,乃知己心略同天心,故其最悲哀者,在其自身看来,则是“此心之在天地间”的无人可授。生时无以遇,则只能等待来日,故又以《俟解》略表隐衷。
船山过世今已三百二十余年,其思想从清末民初开始受到普遍重视,各种势力借船山思想以为自己作说,曾氏之效船山之强调三纲,反清者张扬船山之民族主义,学者亦各因其所好而解说船山,船山生时遭难,身后又倍受误解,时至今日,船山之思究竟何指,船山之心究为何用,依然未甚明了。此即船山之不幸,而又船山之大幸也。余尝谓诸生曰:“经典之为经典,要接受时间之考验。经不住‘经’,就典不成‘典’。”正是船山思想之无限蕴涵,致使有关船山思想之研究,亦或永远没有一致之解说,此正船山永恒意义之所在也。
责编:莫如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