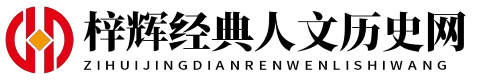(作者:乔凤杰,清华大学教授)
很少有人怀疑传统武术与古代兵家之间的紧密联系,以至于常有人直接以兵家经典来解说武术。传统武术与古代兵家,固然有着不少的差别;然而,在某些方面,却又确实存在着诸多难以分别的相似或雷同。我们无法确证是兵家影响了武术,还是武术有意地依附兵家,但是,却客观存在着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与传统武术一样,古代兵家的经验理性,是由作为价值理性的圣道与作为工具理性的诡道复合而成的。这种复合的理性构架,使古代战争的军事运作与传统武术的技击实战一样,既要遵循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客观规律,又要紧紧地受制于传统道德的约束与规范。
“兵以正出而谲用之”,乃是明代兵学家尹宾商的著名论断。在我看来,此语已经完全道破了与兵家保持着高度一致性的传统武术的理性特征。按常理,探讨武术与兵家的关系,难免要涉及价值理性本身;然而,在我们看来,虽然我们不能完全否定武术与兵家在价值理性层面上有着较深层次的交流,但是,我们又必须承认,两者在此层面上却确实并没有什么源与流的关系。在古代兵家中,真正能够引起传统武术家们重视的,倒是可以移植或嫁接于武术技击中的作战理念与战术思想。
在我们思考武术与战争的起源问题时,将会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因为,对两者之源头的追溯,其实即是对人类暴力产生原因的推测。笔者认为,就源头而言,两者实质是一回事;只是在社会发展与人类进化的过程中,暴力的形式才有了分化:个人之间的导致了武术技击的产生,群体之间的促使了军事战争的形成。这两种同源异流且长期保留着诸多相似之处的暴力对抗形式,必然在对待相同问题的解决方式上,有着诸多相似性的思考。
不难理解,作为军事战争与武术技击之共同本质的暴力斗争,是与人类的产生结伴而来的。人同自然界的其他动物一样,天然地具有为自己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各种条件而斗争的本能。有人生存的地方,就有暴力的冲突与斗争。他们坚信人类在原始群居时就已经存在暴力。作为军事战争与武术技击共同源头的人类的暴力相斗,是人类生存竞争的必然产物。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于是智者诈愚,强者凌弱,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故智者假众力以禁强虐,而暴人止。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师之。”
在管子看来,人类在兽处群居时就已经有了暴力斗争,甚至已经出现原始形态的武术技击与军事战争;而且,此时已经出现了那种出于正义的不得已的武术技击与军事战争。
人类的与斗争,随着社会的进化与变异,自然地表现出了不尽相同的形式。应该说,武术技击与军事战争,并不能代表人类与斗争的全部形式;然而,两者毕竟还是颇具代表意义的。因为,人们在这两种不尽相同的与斗争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而且,不少经验已经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人类在这两种形式的暴力斗争中经历了无数次的考验,已经初具规模地形成了两个独具特色的传统学科。
同源的武术技击与军事战争,必然包含着某种内在的统一性;这种内在的统一性,已经隐含了两者在日后的发展中相互影响与相互促进的可能性。
当我们从根本上去思考两者的实践方式时,不难发现,武术技击,完全可以被看作一种“泛兵论”意义上的军事战争。确切地说,武术技击,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军事战争;而军事战争,其实也就是一种集体化的武术技击。个人之间的生死搏斗,与集体之间的暴力拼杀,在生死对抗的意义上,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客观地讲,已基本进入体育竞技轨道的现代武术散手,其军事战争性质已大大削弱;然而,我们不能否定,作为一种生死搏杀手段的传统武术技击,在其产生与发展的数千年中,一直保持着与古代军事战争在本质上的相似性。毋庸置疑,武术技击与军事战争决不是一回事,然而,在我看来,两者的界线,也只是具有相对的意义。无论是作为生死搏斗手段的传统武术技击,还是足以影响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古代军事战争,都是真实的人类与斗争的具体表现形式,而决不是以友谊与娱乐为前提、严格遵循着某种规则的竞技比赛。虽然我们不得不承认现代武术散手是从传统武术技击中发展出来的一种新的武术技击形式,但是,我们必须清楚,作为一种新的武术技击形式的现代武术散手,就其对抗性质来说,其与传统武术技击之间的差别,可能要远远大于传统武术技击与古代军事战争之间的差别。如果我们仍在保留着对古代神话式的传统武术技击家的万般崇拜,奢望照搬传统武术技击的实战思路来指导现代武术散手比赛的话,那就只能是我们的一厢情愿了;如果我们仍在摇摆着我们骄傲的脑袋,真正地以为我们的现代武术散手是对传统武术技击的全面发展的话,那也只能表明我们这颗脑袋的简单与无知。正是因为传统武术技击与古代军事战争在生死拼杀性质方面的高度一致性,才使传统武术与古代兵家之间的交流具有了可能与意义。
传统武术与古代兵家的交流,准确地说,传统武术对古代兵家的借鉴与参考,是有潜在基础的。现在看来,传统武术与古代兵家最明显的共同点,在于两者都把“正出而谲用”作为了自己的复合理性。“正出”,是说发动军事战争与进行武术技击,要服务于一个高尚的目的,要符合社会的道德规范;“谲用”,是说指挥军事战争与实施武术技击的过程,要遵循其本身所固有的诡诈之道,而不是践行什么成圣成贤的道德规范。传统武术家们与古代军事家早已懂得,虽然武术技击与军事战争都只能是致力于人类和谐的不得已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但是,我们也绝不能把目的当作手段。对于“止戈为武”,我们可以解释为“武”的目的是为了“止戈”,而绝不能说“止戈”的目的是为了“武”。目的与手段,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是不可颠倒与混淆的。
古代军事战争与传统武术技击的实践依据,都是以圣道作为价值理性而以诡道作为工具理性的。孤立地看,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这两个层面上,古代兵家与传统武术,必然都有相互影响的可能。然而,当我们向更深层次挖掘这两种理性的渊源时,不难发现,虽然传统武术与古代兵家之间较深层次的交流使传统武术的价值理性难免受到古代兵家的影响,但是,总的来说,古代兵家与传统武术的价值理性的最终来源,却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当我们谈论古代兵家与传统武术的关系时,虽然必须承认两者具有相同性质的复合理性,但却并不认为是古代兵家的价值理性对传统武术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当然也不会武断传统武术的价值理性对古代兵家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因为,在我看来,实践性很强的古代军事战争与传统武术技击,最本然的理性依据,绝不是什么成圣成贤的道德规范。纯粹的传统武术技击与古代军事战争的最终目的,是要战胜对手,消灭敌人。没有外来规范的这两种生死搏斗形式之间的交流,最容易发生也最容易产生效果的部分,必然是在斗争手段与对抗战术方面。这样,在我们以古代兵家为背景来思考传统武术时,主要关注的,自然是两者之工具理性的交流了。
古代兵家与传统武术的作战思路与战术思想,确有不少相同或者相似之处。然而,我们必须清楚,两者毕竟不是一回事,在诸多方面,还是有着较大差别的。只有在古代兵家把战争的双方当作两个完全融合的整体来思考作战双方的作战思路与战术思想时,古代兵家与传统武术的交流才有了可能。客观地说,两者是不能完全等同的,用兵打仗远比武术技击复杂得多,但却未必会比武术技击更精细。因此,在我们思考两者的必然联系时,切不可有丝毫的夸张。
我们可以肯定传统武术与古代兵家在思想方法上进行交流的真实性,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他们在交流方式上的多样性。
中国古代许多颇有建树的武术家,本身就是伟大的军事家。他们多数有着非常扎实的传统武术根基,接受过系统的传统武术训练。在其所从事的军事斗争中,他们常常把武术技击作为战场厮杀的重要手段。他们在严格地界定两者不同之处的同时,也必然有意无意地把军事战争中的一些战术思想融入到了武术技击当中。集体对集体的军队厮杀,与个体对个体的技击实战,是不尽相同的;作为集体中的一员在参与集体作战时的拼杀方式,与个体直接对敌所进行的自由搏斗,也是不尽相同的。然而,这两种不尽相同的对抗形式中,又同时蕴含着诸多的相同之处。这两种不尽相同的对抗形式之中的相同之处,对于传统武术技击来说,必然是颇有价值的。
对著名爱国将领岳飞来说,他的军事才能与高深武艺,他的岳家军与岳家拳,都是值得人们尊重的。他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自然是对神奇的军事指挥艺术的高度概括,可又何尝不是对岳家拳技击方法的至上要求呢?
明朝著名将领戚继光,撰《纪效新书》,创编长拳三十二式,对军事战争与武术技击均有独到的研究。他不但在武术技击研究中有意无意地融入了不少相关的军事理论,而且还非常重视武术技击在士兵训练中的作用。同时代的抗倭名将俞大猷,更是一个技击功夫与理论造诣颇为深厚的著名武术家。在其有关武术技击的论述中,可以隐约地感受到这位伟大的军事家兼武术家对用兵之道与技击之道的融会贯通。
太极拳创始人陈王庭,早年也是一位军中战将。据陈氏家谱记载,陈王庭退伍还乡后,以陈氏家传拳术和戚继光所创编的长拳三十二式为素材,以太极思想为指导,融合兵家、养生等理念,创建了影响深远的太极拳。虽然,太极拳并非以兵家思想为主要特色,但是,我们决不可以否认太极拳的创建与兵家思想的历史关系。
军事武术家们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但是,传统武术与古代兵家的交流,却远远不是仅限于这些军事武术家们的范围。事实上,传统武术对古代兵家思想的借鉴与吸收,主要还是由那些专业的武术家们来完成的。
或许,在武术理论中引用兵家论述,本身即是思想境界高深的一种标志。传统武术家们对兵家思想的借鉴,更多地表现为对其战术思想的直接移植,或者直接运用兵家理论来论证自己的武术思想。当然,在现存不多的武术资料中,也有一些经过消化与改造后的武术化兵家思想。
人学研究网·中华文明栏目编辑:紫天爵